万千世界只有一个母亲:34位女性作家的母女故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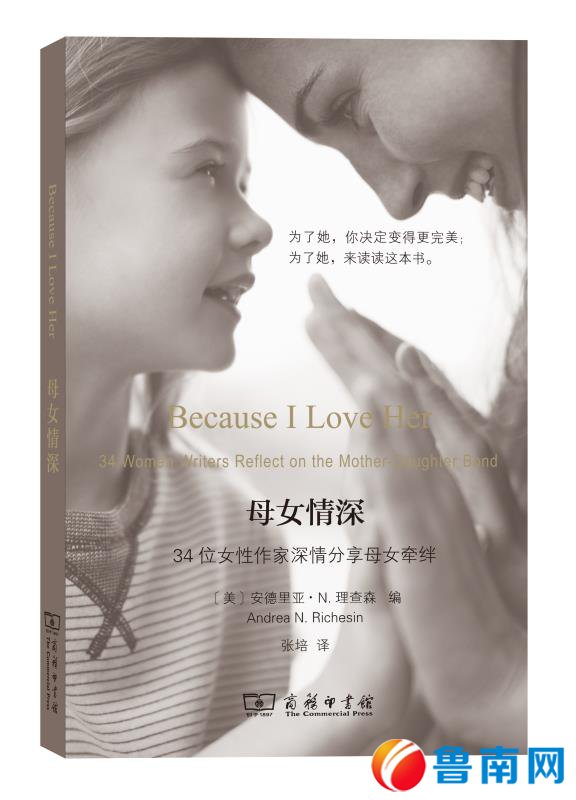
一
“成为女儿,装满妈妈”
杰奎琳·米查德
千百颗露珠迎来了黎明
千百只蜜蜂在花间飞舞
千百朵蝴蝶在草间闪耀
万千世界却只有一个母亲
——乔治.库伯《唯一母亲》
我19岁,弟弟15岁的时候,母亲死于脑瘤。这个恶疾夺走了她的美貌和智慧,感恩节那天确诊,情人节之前她便已经离世了。
作为一个半大的女人,生命中从此失去了最强大的推进力量,面对接下来的人生,我自问:剩下的人生我该令什么人骄傲呢?母亲很严格,给我定了很多规矩:我必须举止得体,衣着整洁,十一岁开始抹粉刺膏,还得坚持做仰卧起坐。她经常说:“记住,孩子,给你取名为杰奎莱茵.肯尼迪.昂纳西斯是有目的的。”很小的时候,就听她说:“肯尼迪夫人一生荣光,而且她的苗条是出了名的。”妈妈对自己在文化上(和身材上)的要求特别高,中学辍学的她坚持学习我们的课本,学拉丁语和俄罗斯文学,她可以翻译墓碑上的外文,还说《安娜.卡列尼娜》是最好的书。如果她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,一定是个企业家。
作为一个母亲,她并不完美。她酗酒,抽烟抽得也凶。她很大胆,50岁了还敢侧空翻。她风趣、迷人、侠义,有时候也很残酷。
一点儿也不奇怪,我嫉妒那些有母亲的朋友,哪怕是很难相处的母亲。
我愿意付出一切换来一个喷了香奈尔香水,到我家对我指指点点的女人。我渴望她告诫我别在背后说父母的坏话,给我织不穿不行的奇怪毛衣,整理我的抽屉,给我做奶酪西红柿三明治,给我的孩子们买又贵又丑的羊毛大衣。
多年来,我渴望着母亲,我到处寻找。对于自己的女儿,我将自己深植于她们的记忆里,这是我所没有的幸福。
你可不能说我是个过度溺爱、令人窒息的妈妈。我鼓励她们登山、潜水、扬帆,鼓励她们接受精神和物质上的挑战,但可不是爱上当地吸毒小混混这类的挑战。
我鼓励她们独立。
但是,当然,她们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妈妈。野餐盒里的叮咛纸条,爸爸不在家时卧室里的家庭影院,分享女孩儿们都喜欢看的书,和12岁的弗兰西出去喝咖啡,陪9岁的米娅买化妆品。我们三个女人经常一起去听音乐会,出差的时候如果可以,我会带上一个和我一起去。我给她们唱妈妈曾经给我唱过的歌,这是我的最爱。
床头,有一本手工制作的书,上面记满了两个小姑娘说过的话,还有我对她们的感受。我知道,她们有一天会找到这本日记,她们会为之流泪(我已经为之流泪了)。但它绝不是我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箴言。我自己手头保留的唯一一张来自母亲的纸是一张杂物单。女儿们将会从我这里得到所有:当两岁的弗兰西得知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小妹妹的时候,她哭了。“妈妈啊,你要送给我一个我啊。”我把这些写了下来。我还写了米娅多么喜欢躲猫猫,我写了四岁的时候,她问我:“我的脚什么时候才能长高到可以穿高跟鞋,妈妈?”我在书里面贴上孩子们照的照片,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只能照到地上三英寸的地方,里面所有的人物都只能看到躯干,看不到头。
女儿们都单纯地认为我会永远活下去。还高兴地表示当她们结婚以后,要我住在她们家的阁楼上。她们高兴地问我死了以后,谁能得到我的什么东西。但是比红宝石戒指和红宝石鞋更珍贵的是妈妈,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她,而当你需要的时候,她就在身边,你不知道这多么幸福。弗兰西和米娅不会只得到几张退了色的照片,如果我活不到看到她们的孩子的那一天,至少对孙子孙女来说我不是个谜,他们会看到我的故事,有声的影像,成捆的丝带,还有菜谱。我虽然不是大厨,但是每周至少有一天会早早起来做香喷喷的蛋糕早点,惊喜早餐的香味会顺着楼梯爬上去叫孩子们起床。米娅有一次跟她最好的朋友说:“你发誓不告诉你妈妈我妈妈怎么做面包片,这可是获过奖的。”
我在制作圣诞节饼干上花了大量的心思,我让每个孩子都动手参与,我们还一起拼了一副有四百多片的意大利饼干拼图。我在她们身边,她们还能真切地感受到我的存在,虽然他们能自己读书了,我还是会给他们朗读《蔷薇盛开的地方》和《格林盖堡的安娜》,还有童谣“地主的黑亮亮大眼睛女儿,在她那乌黑浓密的秀发上,系上一个深红色可爱的蝴蝶结”。
如果有一天,我逝去了,米娅和弗兰西不仅仅曾经拥有过一个好妈妈,她们还会懂得该如何去做一个妈妈。但是,更重要的,我馈赠给她们的最好的礼物——一种强烈地被妈妈围绕的幸福感,一把遮蔽乌云、遮风挡雨的大伞。虽然这是一把无形的伞,只是一些记忆的汇聚,但是,正像我的某位作家朋友不久前所说的那样,“想象所带来的巨大慰籍是无法想象的。”这或许是我们能够拥有的最真实的东西。
二
“孩子,管好你的钱包”
海瑟·丝薇
空空的口袋无法阻止一个人前进,
阻止人前进的,
只有空空的头脑和内心。
——诺曼·文森特·皮尔
诚然,金钱能给人带来力量、名望和特权,但我不想让女儿对穷困感到恐惧。我丈夫和我可能明天就会失去一切。生活往往如此。只要看看跌宕起伏的股市就知道了,财富有时候转瞬即逝,可遇而不可求。
一场龙卷风就能吹毁我们的房子,保险金都补偿不了;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就能拖垮整个家。虽然我清楚,失去了这些,我的生活将变得无比复杂,但是我能应付过去,因为我们已有准备。
我知道,即使失去了一切,我们也会幸福,也会健康,也会充实。我希望女儿大胆一些,接受挑战,走出家门。我鼓励她尝试有回报潜力的事情,不要害怕扰乱已有的生活状态。为此,她必须自信、真诚,与人、食品和金钱建立健康的关系。当她还年轻的时候,我希望女儿学会对欲望提出质疑,学会分辨想要和必需之间的区别,不盲目跟风,怡然自得。总之,我希望她像我母亲那样心灵手巧,勤劳俭朴,但是知道如何放松绳索。
现在,作为女儿的母亲和母亲的女儿,我夹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之间。我伸出手连接起她们两个,在她们的世界中搭起沟通的桥梁,我在她们中来来往往,从她们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。“会过去的。”我会自信地对女儿如是说,因为母亲曾经历过相同的事情。“让我们挥霍一下下吧,这是我们应得的。”同时,我会对母亲如是说。
三
“总有一天,孩子们将会改变”
凯瑟琳·森特
窗外的月光倾泻出
你心中熟知的爱的诗篇。
——比利·柯林斯《永难忘记》
我们家有两个孩子,一个两岁,一个五岁,喜欢光溜溜。在床上跳啊跳,很好,光溜溜地在床上跳,更好;躲在衣柜里,很好,光溜溜地躲在里面,更好。总之,任何事光溜溜的就是最好的。光溜溜地躲猫猫、跑圈圈、光溜溜地刷牙、吃早餐。动物园里的动物就什么也不穿,它们最好。
只有一件事,光溜溜地不好,就是洗澡,穿上袜子洗澡要好得多。
除了洗澡,只要她们能想得起来,就一定会把衣服脱得光光的,享受赤裸带来的特殊的简单的快感,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。
我知道我应该把这些都记录下来。应该把生日会、公园旅行以及其他欢乐的时光,甚至偶尔的悲伤痛苦都录下。保持生活的真实面目。但是,我坦白,当女儿安娜还是小宝宝的时候,那时她刚学会到处爬,我一路拍摄她满屋子爬来爬去,然后她向拿着录像机的我爬过来,把头搞搞抬起,却突然失去了平衡,头重重地碰到了硬木地板上,摄像机被扔在沙发上,接下来便失去了焦距,我的声音响起:“他妈的!妈的,妈的,妈的,妈的!”还有宝宝无休止的哭声,滔滔不绝。
我应该录下的东西太多了,特别是那些我已经记不起来的事情:安娜摆弄印台,结果墨水都洒在身上了。汤玛斯穿上她姐姐演小飞侠的服装,系着腰带,宣布自己是彼得潘。所有这些细小的画面犹如生活之海的浪花,碎了,消失了。
我所记录下来的远远不够。即使我知道,总有一天,这些淘气的小人儿,这些打我一睁眼就开始问东问西、时刻不得安宁的小人儿们会消失掉。当然,不是表面意义上的不见了,他们还在这里,还是我的孩子们。但是,他们长大了。
总有一天,他们将改变,我像所有父母一样对此心知肚明,录像机、数码相机、宝宝日志、储藏室里的宝宝睡衣和儿童涂鸦都对此心知肚明。除了留住能留住的,还能做些什么呢?
生孩子之前,从没想过养孩子是一件如此耗费精力、全身心投入的事。在我心里,老实说, 曾经认为妈妈会帮我带孩子。毕竟,她什么都知道。她才是妈妈,我从来没换过尿布!曾经认为生个孩子会把我也带回童年,但其实这把我带得离童年更远。
我猛然意识到:人不能得到全部。必须舍弃过去,才能迎来新生。又是孩子又是妈妈是不可能的,又年轻又成熟是不可能的,明了现在却同时感受着过去,也是不可能的。不可能,不可能,不可能。
但是,我发现自己的一只眼睛始终盯着已经消失的过去,好像它们随时会再现。好像我年轻的妈妈,那个我成长中熟悉的妈妈,会在某天下午开着她的萨博曼把我们都接上,回到我童年的家去吃意大利面的晚餐。
